近些年中国经济正经历着高速增长到中速增长的转换,在转换期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稳下来后就是中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重要终端产品历史需求峰值的出现,需求结构率先调整;需求结构调整带来需求总量的减速,而供给侧调整较慢,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经过一个时期的去产能,供求达到相对平衡,经济开始进入中速增长平台;这个时候杠杆率过高的问题突出起来,只有把杠杆率稳住并逐步降下来,中速增长平台也才能得以稳定。这样,我们就看到随着增长阶段的转换进程,出现了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依次调整。
国际经验表明,杠杆变动具有长周期特征,美国等国杠杆率的上升到下降经历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其中降杠杆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时间。就中国而言,除了通常经济扩张到收缩的变动外,还要叠加上增长阶段转换和体制转型等因素,这就使中国的杠杆率变动更具复杂性。
中国经济高杠杆背后有着复杂的体制、政策原因。近年来随着经济减速,存在着相当强地通过加杠杆维持增速的动机。首先是追求过高增速的政绩评价体系。保增长主要靠保投资,而保投资则要通过显性或隐性的地方债务加杠杆。其次是政府与国企的预算软约束。这是改革初期就提出的问题,至今未能解决,有些地方和企业借钱的时候就没有认真地想过要还钱。还有房地产、金融等领域泡沫刺激的过度扩张。社会上的流动性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这些领域。货币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不畅,但进入这些领域的渠道却很畅通。最后是企业融资结构和治理结构的缺陷。中国企业的权益资本比重偏低,过多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如此等等。
正确的或好的去杠杆,应当是在稳杠杆、稳正常经营的同时,着力解决高杠杆背后的体制、政策问题,由过度扩张模式转向稳健或谨慎经营模式,提升效率,逐步将杠杆率降低到一个合适水平。相反,如果只是力图在短期内把杠杆率指标降下来,不抓必要的改革,或者像有些地方那样过多采用行政性办法降杠杆,很可能达不到政策初衷,甚至事与愿违,比如由于政府信用支撑的不对称,最应降杠杆的地方政府和国企反而承压能力强,民企受到更大冲击;“一刀切”的降杠杆,在有些地方引起信用收缩,影响到正常经营。
稳杠杆并逐步降杠杆需要一场深刻的改革,也需要金融创新,其中包括切实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相应转变政绩评价机制;打破长久以来存在的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预算软约束;深化金融改革开放,打开更多为民营经济、中小企业、实体经济服务的通道;有效利用国家信用,可考虑增加发行低成本长期建设国债,为政府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资金支持。
目前,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正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由于民营经济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已经举足轻重,应当提出这样的政策目标,即金融体系特别是正规金融系统,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要与民营经济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也可以提出具体指标。实现这样的政策目标不应该也不可能主要靠行政性办法,而是要立足于机制转换,尤其是要有针对性的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允许并支持那些能够对民营中小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金融机构、业态、产品的发展。金融体系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不是要降低经营标准、放松风险控制,而是提出了加快金融改革开放的紧迫要求。
降杠杆既是战略,也是艺术,要在深层改革与短期平衡、打破刚性兑付与避免大范围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对其长期性、复杂性应有足够准备。日本经验表明,既要防止短期过度紧缩导致增速过快下滑,更要防止货币“放水”使降杠杆半途而废。长远眼光、战略定力尤为重要。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的相继调整,是增长阶段转换的三部曲。正确地稳杠杆、降杠杆,将为经济平稳转入中速平台、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本文系其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上的发言)



 国安主场艰难战平亚泰 争冠已无望
国安主场艰难战平亚泰 争冠已无望
 爱与美——爱慕“粉红馨爱”...
爱与美——爱慕“粉红馨爱”...
 戚薇蓝色系造型前卫 目光闪...
戚薇蓝色系造型前卫 目光闪...
 CBA新赛季浙江双雄开门红 稠...
CBA新赛季浙江双雄开门红 稠...
 买车送京牌?留神因违法被扣车
买车送京牌?留神因违法被扣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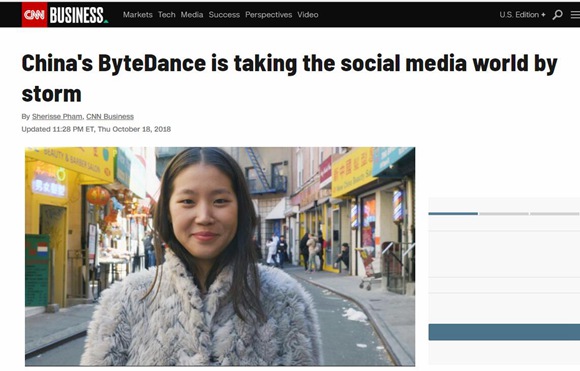 Tik Tok!美媒:来自中国的抖音(2018-11-21 09:50:18)
Tik Tok!美媒:来自中国的抖音(2018-11-21 09:50:18)
 个税专项抵扣实操的三大关键点(2018-11-21 09:50:18)
个税专项抵扣实操的三大关键点(2018-11-21 09:50:18)
 北京中介协会:企业违反...
北京中介协会:企业违反...
 百度杀毒谢幕 不再提供下载
百度杀毒谢幕 不再提供下载
 百余名两岸青年昆明滇池...
百余名两岸青年昆明滇池...
 台铁列车出轨事故已致18...
台铁列车出轨事故已致18...
 荒原创伟业 匠心铸辉煌
荒原创伟业 匠心铸辉煌
 【中国那些事儿】美媒:...
【中国那些事儿】美媒:...
 “第6届海峡两岸水利青年...
“第6届海峡两岸水利青年...
 2018中超联赛颁奖典礼11...
2018中超联赛颁奖典礼11...
 “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
“美丽中国·网络媒体生...
 记者卧底保健品公司:免...
记者卧底保健品公司:免...
 王者荣耀“听见王者世界...
王者荣耀“听见王者世界...
 光明日报:中储粮首届公...
光明日报:中储粮首届公...
 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岸...
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岸...
 27城同“心”暖中国,格...
27城同“心”暖中国,格...
 打游戏时队友吵架了怎么...
打游戏时队友吵架了怎么...
 刺激战场:为给队友复仇1...
刺激战场:为给队友复仇1...
 WPL2018狼人杀职业联赛首...
WPL2018狼人杀职业联赛首...
 英皇电竞菁英杯2018:皇...
英皇电竞菁英杯2018:皇...
 奋起再次创业 目标锁定...
奋起再次创业 目标锁定...